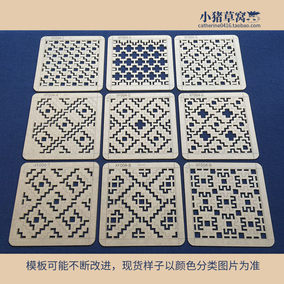生产队有五口水塘,两大三小。
三口小的,水面不足一分地,水深不过膝。说是水塘,实际连小水池也算不上。
两个大的,一个叫老塘,一个叫新塘。水面不过三分地,盘踞在梯田最顶端的两个山坳出口处。
五个水塘的主要作用,是灌溉生产队的十几亩梯田。这些梯田,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山腰。用它微薄的出产,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山里人。
对年少的我们而言,最盼望的,是每年腊月底,生产队干塘。
大人们高挽衣袖和裤腿,光着脚,在塘里边捉鱼,边嘻笑打闹。
“癫子”看到五寡妇走过来,故意一个趔趄,踩进一个脚印凼里。迸起老高的泥浆,溅得她象个泥菩萨。惹得她边骂死鬼,边双手捧水,直往他身上拂。
“短命鬼”更是无聊。捉起一条小鲫鱼,悄悄放进六娘的后衣领里。鱼顺着后背,直向下滑。惊得爱俏的她,尖叫不断。边在水里跳,边提起衣服,把鱼抖出来……
我们这群小孩,来到鱼塘外的水渠里,放一个箕畚,各截一段。捞鱼塘里走漏的“长粒公”(邵东方言,声近字。下同)、“麻粒婆”等小鱼和小虾。
这种捉鱼方式,全靠撞。
排在靠近鱼塘出水口的,收获大点。大半天下来,能捞三五条漏网之鱼,两三只小虾。
后面的,往往人在水渠里全身都冻僵了,提桶里还是空空如也。好不容易捞上一条“长粒公”,那股兴奋劲,无法形容。
在水渠里捞鱼,是为了等大人们干完鱼塘,去“捉野鱼”。
水渠的水流很小了时,塘基本上干完了。
我们来不及顾上早已湿透了的衣服,光着膀子和腿,打着赤脚,围到了鱼塘边。
听到一声喊,塘干完了。就冲到里面去,捉被踩在或钻进塘泥里的小鱼小虾等,捡落下的田螺和蚌壳。
霎时间,鱼塘里泥浆飞溅,一片混乱。
不一会儿,大家都成了“泥人”。露着两个黑洞,一排白色的牙齿。拧着沾满泥浆的提桶,蹒跚地在塘泥里搜寻。
一个下午忙活,收获大的,有半来斤鱼虾。少的,还是那么三五条。
记忆中第一次干塘,是和父亲一起,给别人帮忙。
其时刚好碰到冰冻天气。干塘的日子已一推再推,眼看马上就要过大年了。买鱼的人天天催,塘主也急得直跺脚。
一塘鱼如果不能在过年时卖掉,开春后又不是自己放塘了。那时再来卖,要的人少,价钱上不去,还得赊账。全年的收入,就打了水漂。家里的日常开支所欠的账,孩子来年的学杂费等,也没了出处。
鱼塘的水放得很浅了,万一鱼被冻死或偷了去,一年的辛苦,最后变成了“羊白劳”。
冰天雪地里去干塘,没有人愿意干。
塘主在我家来第三次时,父亲直起身,叹口气,拉着我,答应了。
我当时急于想去,完全是出于好奇。
按照风俗,腊月底请人干塘,主人要选一条最大的鱼,煮一大锅,款待捉鱼的人。临走时,打发一条大草鱼或两条鳙鱼,以示感谢。
帮人干塘,有好的吃,还有拿。对年少无知的我而言,很有诱惑力。
迎着呼啸的北风,赤脚刚踩上厚厚的冰雪,一股刺骨的冰凉,迅疾从脚底升起。冷得人牙根直抖,浑身起满鸡皮疙瘩,剧烈地颤。
走进水没过膝盖的鱼塘里捉鱼,开始几步,还能感到腿脚是钻心地疼。不一会儿,就完全麻木,没有了感觉。
手,也完全冻麻木。一条两三斤重的草鱼,往往要把吃奶的力气,全部费了出来,才能捉到竹篓里去。
围观的人,直笑我们父子,手摸豆腐去了,连条鱼都捉不住。
更有“斗伞方”者,捡起一块石头,故意丢到我们身边的水里或淤泥里,溅得我们一身是水或泥浆。变成“大花胡子”,引得哄堂大笑。
塘主用一个虾筢(邵东方言,音近字,一种用楠竹篾织的渔具。下同),拦在鱼塘的放水口。周边填上塘泥,仔细踩紧,生怕鱼走了。
鱼塘外,塘主的孩子,在水渠里连放了两三个捞篼。
他们在那守着,不准来捉鱼的小孩,越过捞篼捞顺水溜走的鱼。不然,就抢东西。
大半天忙活下来,塘干完了。我看到父亲,全身热气蒸腾。不一会儿,就凝结成晶莹的小颗粒,变成“白毛佬”。
中饭的主菜,是两大碗鱼汤,各点缀着三四条小鲫鱼。
鱼是塘主的女人挑好,父亲剖开,煮的。她怕鱼煮多了,大家吃不完,浪费了可惜。
父亲刚把两碗鲫鱼汤端到饭桌上,塘主的俩小孩,就伸手把碗拖到自己面前。他俩不准别人去他们碗里夹鱼,否则就大闹大骂。
塘主开口,要小孩夹一条给我。话还未落音,女人就大发雷霆了。
说小孩还莫呷东西,就在这说过不停,名堂多。手中的筷子,啪地一声,从饭桌那边,窜到我面前。嗖地飞过我头顶,掉到地上。
父亲见状,劝了一阵。说孩子还小,让他们吃,莫关系。
当晚,塘主偷偷溜到我家,送鱼来了。他解开上衣,从腋窝处拿出鱼:一条鲢鱼,不到一斤;还有三四条小鲫鱼。
塘主反复道歉,要我们父子莫见怪,莫和他女人一般见识。
我和母亲刚想插话,就被父亲喝住了。他呵呵一笑,把鱼挡了回去。要塘主趁早把鱼拿回去,不然两口人又会骂架。
按照家庭联产承包田土时抽签决定的顺序,我家放老塘了。
干塘前,我和弟弟准备效仿他人的做法。把来捞鱼的孩子们,都赶到他们曾经划定的“界线”外。
刚开口,就被父亲骂住了。他不准我们在鱼塘外放捞篼,也不同意我们去守鱼塘出水口的虾筢。
鱼塘外,不时传来捞鱼者的欢呼声。“我捞了一条鲫鱼”,“我捞了一条好大的鲜子”。
我见状,走到守出水口的爷爷身边。伸手探进水中摸了一下,虾筢下面有一条比手指还宽的缝隙。他们捞到的鱼,都是从这里溜走的。
爷爷不准我用泥巴,把缝隙堵上。说难得放一次鱼塘,走点小鱼,没有关系。别人干塘时,我也经常捞人家的小鱼。
干完塘后,父亲马上选出一条最大的草鱼。杀了,煮成一大锅。端出一坛米酒,招待来买鱼的邻居。
爷爷、母亲和我们兄妹,没有上饭桌坐的机会。父亲端来一碗汤鱼,要我们将就下,围坐灶头吃饭算了。
饭后,爷爷和父母一起,站到盛鱼的大木桶边,商议起来。
东边的三爷是组里年龄最大的,一个人了,送条大鲤鱼给他蒸着吃。西头的连先生眼睛不看见,送条草鱼给他过年。下头屋的满嫂丈夫刚过世,自己又有病,四个孩子都还小,蛮可怜,送一条草鱼一条鳙鱼给他们……
边计议,边挑鱼。
送鱼,是我们三兄妹的任务。爷爷和父母反复叮嘱我们,去送时,要轻声细气。从后门或侧门进,前门出。不能要人家的回礼,更不能“啪”地一声丢过去或随意一甩了事。
见我们不愿去送,大人们相视一笑。乐呵呵地说,人,不要小家子气。
爷爷的年龄,在组里排第二。别人干塘时送鱼乡邻吃,从来没有他的份。
“四伯伯,我来送鱼把您呷了!”
他们拎着鱼,从我家门口招摇而过。人还未到,音就先来了。
对此,爷爷和父母总是淡然一笑。他们反复告诫我们,不要去靠别人来送东西给你吃,更不要有什么想法和意见。
大家都困难,日子都过得紧。送,是人家的情义。不送,是本分。
无论怎样,这个地方,是我们一家人的福地。爷爷年轻时逃过好几年的难,去过很多地方。到这里时,好心的乡邻们收留了他。
从流离失所到成家立业,然后再到有了一大家子人。爷爷对这块热土,非常感激。
后来,我家又放过新塘。
干塘时,适逢下雪。
组里的不少年轻劳动力,不待我们喊帮忙,就纷纷挽起裤腿,帮我家捉起鱼来……
作者简介:周志辉,笔名石观音、观音石,男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。曾躬耕杏园十载,后中途易辙,现为公务员。闲时偶尔码字,作品散见报刊杂志和媒体。
特别声明:文中大部分图片,均来自网络,在此向原作者及有关平台和人员表示衷心地感谢。如有侵权或其他事宜,请第一时间持权属证明与本平台或作者联系,我们将及时更正、删除,谢谢。
特别提示:若对本平台感兴趣,敬请长按下面的二维码添加和关注。“乡土记忆”系列文章欢迎转载,转载时请注明出处。
诚挚邀约:从现在起,本平台开辟“乡村那些事”专栏,系统地推介乡土,传承人情,诚挚欢迎各位方家及文朋诗友赐稿。
赐稿邮箱:3450849905@qq.com。

 笔记百科
笔记百科